初审编辑:田泽文
责任编辑:李玉梅
编者按: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淄博市积极响应号召,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特别是2022年以来,组织开展了全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推出了一批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优秀研究作品。为充分展示淄博市社科规划研究工作的丰硕成果,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有为、再创佳绩,特选取部分优秀研究成果予以刊登。
山东历代书院藏书研究
书院自唐代诞生以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班书阁《书院藏书考》曾言:“盖书院之所以名之曰书院者,即以藏书故也。”书院藏书与讲学、祭祀成为书院三大事业之一,又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成为中国古代藏书四大支柱之一。
一、近年来关于古代书院藏书研究现状
自民国以来,古代书院藏书研究得到学人的高度重视,近数十年来,在诸多层面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从总体上对书院藏书进行研究,如班书阁《书院藏书考》是较早进行书院藏书研究的专题论文,论述书院藏书发展的历史、藏书来源、藏书管理,并对部分知名书院藏书进行了评点;杨建东《古代书院藏书概述》构建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院藏书研究的框架,在书院藏书的起源、发展、来源、管理和利用、历史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徐寿芝《古代书院藏书利用探析》认为,“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相比较,书院藏书更重利用,在利用中体现其价值,并在流通中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
在分省研究方面,北京、江西、福建、贵州、云南、河南、河北、湖北、重庆等省的古代书院藏书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多是从藏书来源、藏书管理和藏书意义三个方面对书院藏书进行研究,但大多在理论方面创见不多,有的研究根据本地区书院资料提出了本地区书院藏书特点,如赵连稳、王春福在《北京古代书院藏书探微》中,认为北京书院藏书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除购置外,出版、赐书、搜集是其重要的来源;胡立耘在《清代云南书院的藏书文化遗产》中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遗产三个方面探讨了云南书院藏书文化,“在地方文献整理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分省书院藏书的研究,开掘出了大量地方书院藏书史料,如昆明经正书院、五华书院,贵阳贵山书院、遵义湘川书院等藏书资料,张佐良等在《河南书院史》对元代颖昌书院的藏书进行了专章论述,这种分省研究模式对于今后的书院藏书研究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在分朝代研究方面,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各时期的书院藏书也有较多的涉及,贾秀丽《宋元书院刻书与藏书》是较早专门探讨宋元时期书院藏书的文章,从藏书来源、藏书特色、藏书管理和利用、藏书的历史作用等方面探讨了宋元书院藏书的内容;邓洪波《元代书院藏书研究》认为,“元代书院藏书事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士人加入,藏书楼林立,藏书数量巨大,藏书建设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等时代特点。书院藏书区别于官府、私家、寺观,藏书的公共性、公开性特色也得以突显。”邓洪波、樊志坚《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认为,“明代书院藏书楼建设仍在继续进行”,“院藏书目增多”,“编目则适应情势而求变通”,“藏书制度趋向成熟”,还分析了明代书院藏书不丰富的原因;韩淑举《清代书院藏书初探》认为,清代书院藏书相较于前代,具有分布广、来源广、服务对象广、管理严格、与清政府统治思想和学术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等特点。
在书院藏书征集、管理利用、与学术研究等关系方面,有许多论文把书院藏书与现代图书馆比较,进行了面上的分析,如秦健民《略论古代书院藏书与书院教学、学术研究的关系》中认为,“书院重点收藏教学用书,密切配合教学需要”;“书院藏书为开展学术活动和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书院的学术活动,书院刻印和收藏师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书院聚书、藏书一大特色。”周郁、蔡建国《晚清书院藏书图书馆化述论》认为,“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书院藏书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编目与借阅制度,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出现了图书馆化的趋势。在书院改为学校之后,书院藏书楼变为相应的图书馆以及藏书为新旧图书馆利用,都是晚清书院藏书图书馆化的必然结果。”
还有对于单个书院藏书的研究,有江西鹅湖书院、安徽毓文书院等,如王立斌在《鹅湖书院历代藏书考》中对书院历代藏书的经部善本十九部、史部善本三十九部、子部善本十五部、集部善本七部、别部善本十六部分别进行了考证辨析。
虽然已经有以上不少关于古代书院藏书的研究,但在山东古代书院藏书方面,不仅没有单独的研究,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山东古代书院藏书史料的使用极少,且有不准确的地方出现,因此有必要对山东古代书院藏书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研究,发掘学界所忽视的山东书院藏书资料,以论证山东书院藏书的特点。
二、山东历代书院藏书特点
山东书院起步很早,唐初大将李靖在临朐(今淄博沂源境内)的读书处——李公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建立的书院之一,宋元时期,山东书院发展迅速,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山东历代书院创建数量,诸家学者统计不一,如白新良先生统计为304所,王炳照先生统计为251所,赵承福先生统计为214所,笔者通过系统梳理,认为山东地区历代书院创建数量如下:唐代1所,北宋7所,金代1所,元代27所,明代113所,清代223所,还有创建时代不明的书院21所,共计393所。
唐初建立的李公(李靖)书院,虽然是有史可考的山东最早的书院,但史料记载非常简略,《(嘉靖)青州府志》记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闾左,于此阅司马兵法。”正如《(嘉靖)临朐县志·古迹》记载:“然其事不可考矣。”李公书院只能说是唐初大将李靖读书之所,与书有关,但还谈不上藏书的功能。
到北宋时,承五代战乱之弊,官学不振,书院的兴起替代了官学,泰山书院、徂徕书院等书院因之而兴。北宋景祐四年(1037),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构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可以看得出,泰山书院自建立之始,藏书即为首当其冲之要事,这关系到孙复传道授业之大事,“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复传之于书,其书大行,其道大耀”(石介《泰山书院记》)。孙复在泰山书院讲学期间,撰写了《春秋总论》《春秋尊王发微》等著作。作为孙复的挚友,石介不仅大力支持孙复在泰山书院的讲学,率群弟子师事孙复,还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创建徂徕书院,聚徒讲学。南宋范成大将徂徕书院与金山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一起称为天下四书院。邓洪波认为:“泰山、徂徕书院是一个学派的基地……史称宋明理学开启于宋初三先生,而三先生在泰山的学术活动,实开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先河,值得重视。”泰山和徂徕书院的藏书,主要是孙复和石介个人所藏,正如元欧阳玄《贞文书院记》所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泰山、徂徕书院的藏书,以儒学书籍为主,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应天书院等书院比较相似,书院藏书得到创建者足够的重视,藏书较为丰富,讲学与藏书完美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对于宋代理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元代,蒙古统治者大兴文教,元世祖曾诏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书院设山长一员。”元代书院藏书较之宋代,一是书院藏书数量巨大,远远超过了宋代。至元三十年(1293),东平教授马栎庵创建汶上圣泽书院,“构堂藏书,以授生徒”,“藏书千余卷,构亭讲诵”;恩县会斋书院建立者张汝卿“好蓄经史,匾其堂曰:‘万卷’。立文会斋于堂右,四方贤士有来假阅其书者,则馆于其斋”,书院藏书不仅服务于书院学子,而且对社会上士人也开放。二是蒙古等少数民族士人参与到创建书院中来,且在书院藏书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延祐元年(1314),蒙古贵族、历山公千奴在濮州历山下创建历山书院,“筑先圣燕居堂于历山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书院不仅教授经史之学,还教授医学知识,藏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医书。邓洪波认为,元代书院藏书进入正规化、制度化的阶段。
明代山东书院藏书以个人藏书为主,如鲁藩在兖州所建承训书院、养正书院,章丘的中麓书院等。明嘉靖年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李开先罢官之后,回到家乡章丘,创建中麓书院,书院内建藏书万卷楼,“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昈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时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李开先是明代知名的藏书家,他按汉代刘歆《七略》之法对其藏书进行了分类,因藏书楼空间有限,只收藏经学、时务类的书籍,其他书籍则放置其他地方;李开先还是著名的曲作家,利用当地民间小曲的形式,写成《中麓小令》一百首,还有传奇戏曲《宝剑记》传世,李开先的藏书中当有不少戏曲文学类的书籍,中麓书院藏书之丰富可见一斑。明万历年间,都御史李邦珍致仕,回到家乡肥城,在金牛山创建同川书院,“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我同志及我子孙讲习其中”,对于创建书院的目的,李邦珍在《同川书院记》中说的很明白,“后之为余同志,为余子孙,有登余之堂、读余之书者,当知先余之修而修,然后余之乐而乐,庶几斯院之建,不为无益也”,李邦珍泽被后学之意溢于言表。明嘉靖年间,御史王应初辞官在家乡朝城县建南泉书院,“令延邑中士力不能辟地结业者群入肄习,公又博积经史于其中,以便学者”。
清代是山东古代书院发展的最高峰,书院建设遍布全省各府州县,几乎达到了全覆盖的程度。清初,鉴于明末东林党清议朝政之弊,统治者严禁聚众讲学,反对空谈清议,“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清帝多次下诏,倡导经史之学,书院教学回归到苦读经书、穷究理义的路子上来,因而书院藏书得到各方高度重视,特别是自乾隆以后,书院得到官方的认可,乾隆元年上谕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从省会到府州县,书院发展迅速,书院藏书也成为书院建设的重要方面,获得书院建设、运行各方的高度重视,不仅积极筹措藏书,而且将书院藏书记载于志书,勒之碑刻,希望传之久远。清代山东地方志关于书院的记载中,往往详细记录书院藏书数目、数量,对于书籍的包装情况也有记载(有无函套),如《(道光)济南府志》中有济南泺源书院藏书的详目,《(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和《(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均记载了新任城书院藏书目录;有的书院对于重要的购书、捐书行为还撰有藏书记文,予以浓墨重彩的记载。书院藏书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保存文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藏书之要,首先在藏,即书籍的保管,山东历代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场所的建设,有条件的书院大多有专门贮存书籍的藏书楼或藏书室。元末,朝城人楚惟善所建雪林书院,院内建五车楼以作藏书之所,《(康熙)朝城县志》记载:“雪林书院,在县治东北城下,学士楚公惟善与其子樟读书处,内有七聘堂、五车楼,久废。”明代,章丘李开先建中麓书院,内建藏书万卷楼,并作《藏书万卷楼记》以记其事。进入清代之后,书院内专门的藏书场所更为常见。青州松林书院内建有四书斋,作为藏书之处;临清清源书院在东北隅建有藏书楼;武定府敬业书院设置藏书室三间;沂州琅邪书院建有书室三十楹;德平白麟书院有东西书室各三楹;阳信锄经书院讲堂之西偏室为藏书室;峄县知县张玉树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增建峄阳书院,建堆石书屋,存书于此;嘉祥宗圣书院正殿后有养志楼,上藏御书;光绪十七年(1891),河道总督许景祎创建济宁池楼书院,在池南建楼三楹,以备藏书。
三、山东古代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
对于书院藏书研究,首先要涉及的就是其来源问题,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研究,比较成熟的观点,如班书阁认为,御赐、官吏向各官书局之征集、官吏捐置、私家捐置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杨建东认为,书院购置、书院刻书、捐置图书、皇帝御赐图书是藏书主要来源;邓洪波认为,书院藏书来源主要是五个方面,一是皇帝赐书,二是官府置备,三是社会捐助,四是书院自置,五是建立图书基金;赵连稳认为,书院藏书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捐赠,捐赠又分朝廷颁赐、官吏赠书、社会人士赠书、捐赠捐项与田产;一种是书院购置和刊刻图书,此项又分书院购置书籍、书院刊印书籍、书院抄写书籍。各说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具体到山东书院方面,尚有可商榷的地方,考之史料记载,笔者认为,山东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官府置备
皇帝赐书是书院藏书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以往的学者往往将其单列,但实际上皇帝是官府金字塔的最高一级,因而皇帝赐书实际上应归于官府置备一类。能得到皇帝赐书的书院数量较少,且赐书的数量在书院总藏书量中也并不占主体。据史志记载,山东历代书院中得到皇帝赐书的仅有明代鲁藩所建承训书院和养正书院。养正书院,为辅国将军朱当灞所建,“当灞于府第外架楼贮书训子。嘉靖六年(1527),鲁王转奏,敕建,赐内帑、书籍”;承训书院,为镇国中尉朱观熰所建,《明史》记载:“镇国中尉观熰,字中立,居母丧,蔬食逾年,哀毁骨立。尝绘《太平图》上献。世宗嘉奖之,赐承训书院名额并《五经》诸书。”同样得到了嘉靖帝的赐书。这两所书院虽有书院之名,但却并无书院之实,对社会的影响很小。
官府为书院置备书籍是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主要是指清代山东书院藏书而言。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下诏,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在省会建立书院,并各赐建院经费一千两,书院经费可从公用经费支用,“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诏令各督抚动用公银购买、刊印《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颁发给省会书院。乾隆九年(1744),又诏令将颁发的《尚书》《诗经》《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颁赐到全国各书院。泺源书院为山东巡抚岳浚所建省会书院,泺源书院藏书中很大一部分即由朝廷所赐经费和地方公款所购置,藏书中多有以上皇帝诏旨要求购置之书,如《钦定书经》《钦定诗经》《钦定礼记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周礼义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春秋》《钦定孝经衍义》《御纂性理精义》《钦定数理精蕴》《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以及自《史记》以来的历代官修史书,还有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济宁新任城书院为驻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所建,其藏书也多为官府置备,在济宁的书院中藏书尤为丰富,“所颁《四经》《三礼》以及《十三经注疏》具在,无待外求。”至清代,官府置备这一书院藏书途径,已经成为书院藏书的第一来源。康熙五十三年(1714),山东巡抚蒋陈锡为泰安青岩书院颁发《御纂朱子全书》,此书于康熙五十二年编成,颁发两京及直省刊版通行。乾隆年间,泰安知府王一䕫在重修青岩书院后,又为书院购置了部分经籍;高唐州知州为鸣山书院购置“《御纂五经十三经注疏》《古文选本》,并借备《五礼通考》《佩文韵府》等书存院。”阳信知县曾广运筹措经费,为锄经书院购置书籍,“抽官规以益款项,渐为购置经史凡若干卷,存于锄经书院讲堂之西偏室。”商河县训导孙庆龄筹款重修麦丘书院,为书院购书数十种。值得注意的是,书院藏书还有一部分是从官学拨付给书院的,而官学所藏书籍多为官府刻印颁发的刊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淄川知县盛百二应士绅所请,将官库所存《御纂四经性理》各一部、《钦定三礼疏义》一部、《御制诗》(初集一部、二集一部)捐入般阳书院,供士子诵习之用。夏津大同书院所藏书籍中有一部分也是原官学所存,“历年颁发及历任捐购各书,如钦颁并方公所捐……旧存贮学署,后归大同书院。”据《(乾隆)夏津县志》记载,历年钦颁书籍有《学政全书》一本、《圣谕广训直讲》一本、《御制朋党论》二本、《明史》一部、《四书文》一部等;乾隆四年(1739),知县方学成捐资购置《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御纂性理精义》各一部。从中可见,大同书院的这部分藏书完全是按照官府要求置办的。
(二)个人捐赠
个人捐赠书籍是山东古代书院藏书中重要的来源之一,仅次于官府置备。个人捐赠又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一是书院创建者捐赠书籍。宋元时期,山东书院多为个人所建,书院藏书多由个人藏书而来,个人捐赠是这一时期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宋代,泰山书院的藏书由孙复集聚收藏。元代,武城弦歌书院、汶上圣泽书院、濮州历山书院、郯城曾子书院、乐安明诚书院等三分之二以上的书院为个人所建。元泰定二年(1325),武城善士王仲出资兴建弦歌书院,此后,王仲之子王昺扩建书院,书院藏书完全由王昺置备;元延祐元年(1314),历山公千奴在濮州建历山书院,万卷藏书全部为个人所藏。恩县会斋书院为元代隐士张汝卿所建,《(宣统)重修恩县志》记载:“张汝卿,号澹斋,家饶裕不仕,好蓄经史,匾其堂曰:‘万卷’。立文会斋于堂右,四方贤士有来假阅其书者,则馆于其斋。诏旌其门。”延至明代,这种情况依旧存在,章丘中麓书院为明代太常寺少卿李开先所建,书院藏书全部为李开先所藏;明万历年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邦珍致仕后在家乡肥城建同川书院,聚书千卷,李氏子弟及乡人在书院研读学习。朝城南泉书院为御史王应初建,《(康熙)朝城县志》:“南泉书院,在迎薰门外里余,柱史王公应初教授生徒于此,后公游宦,乃令延邑中士力不能辟地结业者群入肄习,公又博积经史于其中,以便学者,故时多所造就,又称之为义塾云。”清代一些个人所建书院,如淄川绅士陈士隆所建翼经书院、肥城明经栾条所建后山书院、东阿绅士房嵋所建吾山书院、费县绅士郭翘楚等所建东山书院等,或为义学,或为义塾,或为私家别业,其书院如有藏书当系私家捐置。
二是现任或离任官员捐赠书籍。清康熙年间,山东学政徐炯捐俸修济南白雪书院,将家藏书籍全部捐赠给白雪书院,张贞《重修白雪书院记略》云:“公(徐炯)父大司寇公博学嗜古,家多秘籍,六经传注购致尤勤,网罗汉唐以来诸家笺疏数千卷,刻之家塾,卷帙浩繁,世人罕觏,公取全部庋之后阁,恣学者翻阅,以广见闻。”清道光年间,已经升任山东按察使的李文耕为曾经任过职的冠县的清泉书院、邹平县的梁邹书院颁发所刻《朱子全书》等各种书籍;武城知县傅士珍捐廉,为弦歌书院代购三十余种书籍。咸丰年间,高密知县周寅清在离任后,仍为高密夷安书院捐赠《皇清经解》,周寅清在《寄薛文堉书》中说:“近阮芸台夫子纂刻《皇清经解》,荟萃菁华,诸名家为郑学阐明不遗余力,用寄夷安书院一部,计四十函。”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举人姚光浚任齐河知县后,“购书籍百余部捐置督(扬)书院,以便士子取阅。”光绪十六年(1890),屠义炳在代理陵县知县期间,为县三泉书院捐赠书籍,“捐《汉书》《朱子纲目》《绿野斋文集》等书,存诸书院。”夏津知县范一双向大同书院捐十数种书籍,有《紫阳纲目》《佩文韵府》等;知县赵尔萃“整理书院,广购书籍”,向大同书院捐赠百余部书籍,有《孙吴兵书》《太公阴符》《六韬》《黄石公授张子房素书》与诸葛亮所著书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胶州知州张玉树创建胶西书院和灵山书院,并为两书院置备书籍,“购书数千卷,分贮之。”这些为书院捐赠书籍的官员,无论在任或离任,内心无一不充满了对任职地方文教事业的关心。平阴知县张朴在重修云门书院后,作记文说:“士君子学古入官,所以见诸措施者,无论才具大小、器量广狭,要惟初心不可负,本色不可失,而生平服习之地,其功能为素娴,其利弊尤深悉,则读书人任读书事,是只以本色全初心,而政之要得焉,此固责有难谢,而事所乐为者矣。”笔者曾论述士大夫与山东书院建设的关系,提出以下观点:“士大夫积极参与创建书院原因,主要是兴学重教的职责所在、社会教化的需要和儒生本色的体现。”盛百二是清代知名学者,曾任泺源书院、任城书院山长,《(乾隆)淄川县志》记载其任职淄川知县期间,“退食之暇,不离书史,盖以文学为政事者。”为书院置备藏书,是士大夫积极参与书院建设的重要方面。班书阁《书院藏书考》说:“书院之藏书,出于官吏捐置者,惟清为盛。”
三是本地绅士捐赠书籍。道光二十三年(1843),福山县举人、曾任陕西醴泉县知县的杜宗岳向福山宾阳书院捐赠书籍二十三种,《(民国)福山县志稿》详细记载了捐书目录,“《御制文集》《十三经注疏》《礼记义疏》《周礼辑义》《仪礼参义》《周易辨录》《春秋集义》《史记》《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困学纪闻》《孟子注疏》《朱子纲目》《资治通鉴》《宋元通鉴》《文选》《读史快论》《明史》《二程全书》《张子全书》《呻吟语》《人谱》《佩文韵府》”,在“书院款项无多,膏火甚微”的情况下,书院无力购买书籍,这些捐赠书籍构成了宾阳书院藏书的主体。
(三)书院自置
书院藏书除官府和个人捐赠之外,书院根据需要自行置办也是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书院自置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书院自购。书院的运转需要一定的经费,来源往往来自官绅捐资、学田之租息、发商生息之息金等,这也是邓洪波所概括的“图书基金”。冠县清泉书院的藏书大部分来源于自购。据《(民国)冠县志》记载,“清光绪季年,吾冠购书百余种,皆精印善本,藏之清泉书院。”博兴锦秋书院购置了《十三经》《皇清经解》以及前四史等书。寿张县寿良书院藏书有一大部分是用兖沂道锡良的捐资购买的,锡良视察寿张期间,看到寿良书院遇灾重建后,因经费短绌而没有藏书,捐二百金,用作书院购书经费,《寿良书院藏书记》:“寿张书院立已有年,黄水入城圮而复建,院鲜书籍,考镜无资,适逢升任长白锡公印良观察兖沂,濒行,捐金二百,为购书籍之需……爰举赐金购书十二部。”寿良书院还动用公项,从山东志书局购置了书籍若干册。
二是书院刻书。书院刻书由来已久,但限于书院经费有限,能够进行刻书活动的书院较少,但书院刻书无疑是书院藏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书院藏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明代中麓书院创建者李开先曾刻书七种,如边贡《华泉集》等;明代鲁藩所建书院中也多有刻书者,如承训书院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刻《抱朴子》,隆庆三年(1569)刊刻《海岳英灵集》,养正书院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刊刻《金精直指》,敏学书院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刊刻《张先生校正杨实学易传》;平度太泉书院创建者官贤刻龚大器《新刊招拟指南 新刊比部招拟》;即墨东崖书院创建者蓝章刻胡炳文《云峰胡先生文集》和自撰《八阵合变图说》;潍县麓台书院创建者刘应节刻丘橓《新刻月林丘先生家传礼记摘训》。清代,山东书院刻书数量较之明代更多。济宁任城书院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主讲盛百二所撰《尚书释天》,并藏书两本;曹州重华书院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刊刻山长余鹏年所撰《曹州牡丹谱》;黄县士乡书院在同治年间曾刊刻《士乡书院志》,这是山东书院唯一自刻书院志;青州旌贤书院在光绪十九年(1893)曾刊刻《益都丁壬集》三卷并《菊社诗》一卷。这些书院刻书都进入书院藏书之列。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作为省会书院的泺源书院在清代刻书活动比较多,据唐桂艳统计,泺源书院共刻书八种,其中乾隆年间五种、道光年间一种、同治年间二种,孟鸿声主编《泺源书院志》统计,泺源书院刻书十九种。同治八年(1869)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建尚志书院后,尚志书院刻书三十五种。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前后相接,所刻书籍不仅丰富了各自书院的藏书,而且还行销省内各府州县书院,成为各级书院藏书的一部分。丁宝桢于同治九年(1870)创办的山东书局共刻书42种,加上子目,达七十余种,山东书局所刻书也是山东各级书院在同治光绪年间藏书的重要来源。此外,书院刊刻的师生课艺文章也是书院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泺源书院在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刊刻过《泺源书院课艺》五编,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都曾为之作序,足见对刊刻书院课艺的重视,山长匡源在《泺源书院课艺三遍》序中说,此书刊刻后,“一时学者争先快睹,翕然成风,几于家置一集”;肥城知县杨延俊选刊鸾翔书院优秀课艺文章,刊刻《鸾翔书院课艺》,该书“远近风行,家有其书”;武城弦歌书院条规规定,“课卷取列超等,留于监院处,每届年终,敦请山长校阅一番,拔其尤者,刊为《弦歌书院课艺》,年复一年,汇而成帙,庶几观摩有自。”据青州一中馆藏清代松林书院藏书可知,松林书院曾收藏有《格致书院课艺》等其他书院的课艺刻本。恩县知县陈学海建近圣书院课士,刊有《贝州课艺》。其他如武定府敬业书院、蒲台萦蒲书院、文登文山书院、济宁济阳书院、潍县麓台书院等书院刊刻课艺之书者众多,这些书院刻书也成为书院藏书的一部分,且成为最受欢迎、阅读最多、最为实用的部分。
四、山东书院藏书构成
(一)书院藏书以实用性书籍为主
书院藏书以实用性为置备基本原则。武城知县傅士珍为弦歌书院购买书籍的原则,即是“择其要者”,何为“要者”?即书院生徒阅读必需用书,也就是满足科举需要的书籍,此外才能徐图其他书籍。清代河南开封大梁书院的《购书略例》说的更为明白:“书籍期于有用,上之研穷性理,讲求经济,次之博通考据,练习词章,四者,其大较也。近刻种类日繁,备购匪易,先择其最有用者购之。”清代很多书院建立的初衷,即是改变科举不利的现状,淄川般阳书院即是如此。长期以来,淄川科举不振,“及分校午闱,淄之登贤书者,无闻焉。”知县周统认为这是士子“肄业无地、育才无方”的缘故,故而创建般阳书院,希望淄川能够“甲第蝉联,人文彪炳。”因而科举用书是书院藏书的首选用书,后任知县盛百二将《御纂四经性理》《钦定三礼疏义》等书捐入书院。高密知县周寅清卸任后给夷安书院寄回一部《皇清经解》时,认为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书院还需要再购置《十三经注疏》,以备生徒阅读。这些书是科举时代士子的必读书。
以寿张县寿良书院藏书为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寿良书院购置书单如下:
《御选通鉴纲目》全部四编十八函百三十四本、《子史精华》三函三十二本、《钦定佩文韵府》(拾遗附)两箧二百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四函二十二本、《皇清经解》(连编目)九函六十八本、《经余必读三编》一函十本、《皇朝经世文正续编》十八函一百二十八本、《汉魏丛书》十二函一百二十本、《国朝先正事略》一函十本、《曾文正公全集》十二函一百二十八本、《昭明文选》一函十二本、《海国图志》三函三十六本、《圣武记》一函四本、《山东考古录》一函六本、《山东军兴纪略》一函十本。
寿良书院购置的书籍都是以实用性为主,如《寿良书院藏书记》所说:“学问之道无穷,书籍亦无穷,惟切于用者而购之。”博兴锦秋书院的藏书也非常得实用,都是生徒日常使用之书,兼顾了经史子集,藏书书目如下:
阮刻宋本《十三经》十二函计一百八十二本、《皇清经解》四十函计三百六十本、古香斋《史记》四函计二十四本、《前汉书》二函计十六本、《后汉书》二函计十六本、《三国志》一函计八本、《二十二子》八函计八十三本、《古文词汇纂》一函计十二本、《唐宋文醇》二函计二十本、《唐宋诗醇》二函计二十本、《汉魏丛书》八函计六十四本。
锦秋书院藏书中仅有前四史,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书院学子能够读到这四部经典史书也是难能可贵的。高密通德书院的藏书更为精要:
《十三经注疏》十六函、《皇清经解》四十函、《康熙字典》六函、《四书汇参》四函、《朱子全书》六函(带盒)。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阮元任江西巡抚时主持纂修的大型丛书,《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以所据版本丰富著称。《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或《清经解》)是道光初年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建学海堂罗致学者所编纂,该书汇纂七十三位学者、一百八十三种著作,1400卷,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道光九年刻成以后,便成为读书人或书院的重要藏书。书院往往根据自身经济情况,选择购置数目,如滕县道一书院购置了十七史一部、九通一部。虽然记载很简单,但十七史实际上是自《史记》以来的历代官修史书,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九通指的是:《文献通考》《通典》《通志》《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从这样的藏书内容可以看得出,道一书院对于经史之学非常的重视。
(二)书院藏书反映捐赠人的藏书兴趣、个人品味
元历山公千奴建历山书院藏书中不只有经史之书,还收藏大量医书,程巨夫《历山书院记》:“历山书院以成……再舍而谒医,以防有疾,复藏方书。”历山书院的藏书成为元代书院藏书中一个显著特色。弘扬医学实际上是元朝统治者提倡的结果。《元史·选举志一》记载:“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猷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其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济南泺源书院藏书中有《潜研堂诗文集》《香树斋诗文集》《莲龛集》《忠雅堂文集》《忠雅堂诗集》《玉茗堂全集》等不少集部著作,很可能就是个人藏书而捐入书院者。陵县三泉书院藏书中有《绿野斋文集》,即为代理知县屠义炳所捐。夏津知县赵尔萃向大同书院所捐《孙吴兵书》《太公阴符》等兵书可以说体现了赵尔萃的个人兴趣。福山宾阳书院藏书中的《读史快论》《人谱》等书为福山绅士杜宗岳所捐赠。这些在科举应试以及经史之外的藏书,虽与科举考试关系不大,但对于书院学子广泛阅读、开拓知识面有重要的作用。
(三)书院藏书与所奉祀先贤有关
书院自唐宋时起,书院建设与先贤名宦遗迹多有关联,笔者曾就先贤名宦遗迹与山东书院建设两者关系进行专题研究,认为:书院建成后,出于表彰先贤、歆仰后学的需要,书院兼有祭祀的功能,书院藏书中往往以先贤著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郯城县西北磨山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讲学处,元至正二年(1342),邑人管文通即地建曾子书院,“庐陵士又有郭元辅买书籍若干部,刊曾子所著书若干卷,今皆藏于曾子书院云”(元·刘诜《曾子祠记》),“元人亦建书院,设祭器,藏所著书于其中”(明·王天爵《重修一贯书院记》)。书院藏书中重要部分是曾子所著书。邹平伏生书院以纪念伏生而立,书院中生徒以攻读《尚书》为业,清人施闰章《修伏生祠记》:“时诸生数十辈,皆治《尚书》。”从中可知,伏生书院藏书中应以《尚书》类为主。莱州东莱书院以纪念吕祖谦而立,书院要求生徒研读吕祖谦的著作,明人赵秉忠《重建东莱书院记》言:“后之髦士肄业其中,颂先生诗,读先生书,习先生礼器,如见先生者。”吕祖谦的著作必然是书院重要藏书。清乾隆三十年(1765),桑调元在担任济南泺源书院主讲期间,主持刊印其师劳史(字麟书)的著作《馀山先生遗书》十卷(须友堂刻本),据《(乾隆)历城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山长桑调元建朱子祠于后,以陆龙(陇)其稼书、张履祥考天(夫)、劳史麟书三先生配。”桑调元曾主讲开封大梁书院、济南泺源书院等书院,在其任内,皆建须友堂(劳史堂名),以奉祀其师。桑调元不只在书院奉祀其师,还主持刊印其著作。桑调元还主持刊印了海宁沈翼机的诗作《澹初诗稿》八卷,桑调元作为其门人,为之作序。
(四)书院藏书重视地方文化
编纂、收藏地方志书是反映书院地方特色的重要标志。清康熙年间,益都知县陈食花任职期间,开县志局于云门书院,主持编修《益都县志》,阅三月而书成。光绪年间,肥城前知县邵承照在卸任知县后,主讲鸾翔书院期间,主持编纂了《肥城县志》。济南泺源书院藏书中有《旧济南府志》一部十六本,济宁任城书院藏书中有《济宁州志》一部、《济宁直隶州志》一部。宁津县在清代隶属直隶河间府,临津书院藏书中存有《畿辅通志》一部。许多书院还收藏有山东学者所著书或与山东有关著述,如寿张寿良书院从山东书局购进顾炎武著《山东考古录》一函六本;济南泺源书院收藏有清山东学政陆燿《切问斋文抄》一部十本、乐陵潘伍云《山左诗续抄》二套十六本、明山东巡抚胡缵宗《鸟鼠山人全集》一部二十二本、滋阳牛运震《空山堂全集》一部三十六本等书。
(五)近代山东书院藏书趋向多元化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以研习儒学为内容、以科举出仕为目的的传统教学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山东书院藏书内容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同治、光绪时期,书院藏书结构较之清前中期,有较大不同,西学、时务等书籍开始进入书院藏书之列。肖永明曾指出:“书院藏书往往更注重实用,在内容上更具有时代性、反映时代发展要求。这一点,在社会转型、时代思潮发生变化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光绪二十五年(1899),寿张县寿良书院重建后,从兖沂道锡良所捐款项里购置了魏源所撰介绍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的《海国图志》一套;宁津临津书院不仅购置了《海国图志》,还购置了清末数学家华蘅芳《算学笔谈》、英国华里司《代数术》以及《新译几何原本》等西学之书。同光时期,正值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运动之后,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国人来讲尤为重要,《山东军兴纪略》等记载镇压农民运动的书籍也为各级书院所青睐,进入寿张寿良书院等书院购书之列。为改变重文轻武的局面,古代兵书也成为书院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书为宁津临津书院收藏。
五、山东书院藏书管理与利用
书院藏书与私人藏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力求藏书物尽其用,不仅为了藏,更重要的是为了用,因而书院藏书在管理上往往对借阅者敞开大门,欢迎借阅。书院往往要求学子广泛阅读,如莱芜汶源书院创建者、知县纪淦所说:“目未睹古今大儒名贤之著作,则所见不真,胸不悉廿二史之治乱是非,则所论不卓。”武城知县傅士珍为了让书院学子广泛阅读,捐资购书,“在院肄业寒士居多,苦志攻读,购书为难,公(傅士珍)重惜其根柢之不深也,因再捐廉,择其要者,代购三十余种,发存书院,俾周观览。”博兴知县李铨认为:“不得经史以槃深其根柢、子集以陶淑其性灵,则孤陋寡闻,未易经言造就矣。余深知寒士读书之难,读书而得善本之尤为不易,爰于旧存经史子集中,各择数种置之院中,诸生有志实学者,可来院翻阅,以资考证。”山东学政徐炯将家藏数千卷珍稀书籍捐赠白雪书院,“恣学者翻阅,以广见闻。”可以说,书院藏书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书院师生研究学问、广泛阅读而服务的。
(一)书院藏书的管理
山东古代书院藏书管理制度略显粗疏,从某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书院记载上看,大致有以下三项:
一是书院藏书向生徒公开书目,并制定借阅规则。济南泺源书院悬挂巡抚陈预捐书数目木榜,博兴锦秋书院“捐置书目镌石列书院讲堂壁间”,峄县峄阳书院“前令张君玉树存书四十五种,马君有绂作书院规条,碑之前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借阅者对藏书有所了解,使借阅有的放矢。阳信锄经书院为鼓励士子借阅藏书,甚至对借阅多者有奖励,“令诸士子披阅,勤者有奖励。”书院还要求借阅人要爱护书籍,书籍只能在院内查阅,不能带离书院,以免散失。高唐鸣山书院规定,“如有查阅者赴院摘抄,无得各自携归。”博兴锦秋书院也规定,“诸生有志实学者,可来院翻阅,以资考证,不准携归私第,俾免散失之虞,诸生其永宝之。”
二是书院藏书有借阅期限、损坏赔补等规定。宁津临津书院规定,“凡生童借阅书籍,限一月交还,其于借时之检取,还时之收庋,务当随时登记,仔细检点,不得任意延忽,设或残缺散佚,必须根追赔补,庶可历久无失。”高密夷安书院规定,“借观宜遍也,琅函存贮,庋阁其中,牙签抽紫,灯火分红,借书迟送,古有醇风,循环注部,流转无穷”;“翻阅宜慎也,涨痕旧渍,予念怀惭,油污墨染,蠹蚀同贪,亟宜收拾,无损瑶函,不准重借,法立严严。”
三是书院设藏书管理人员。宁津临津书院规定,设置专门的藏书管理人员,由生徒中学业优异者兼任,给予一定的薪资,类似于现今高校图书馆之勤工俭学岗位,“书院存书设斋长一人经管,年终予辛资一百四十四千,俾得常住书院,以专责成,以岁考列第一者为之(设有枪替幸取者,不准冒充),如第一有故不就,则以第二第三代之,三年一易。”高唐州鸣山书院也规定,各种书籍开列目录,“送存备查,派住院者一人收管。”
(二)书院藏书的流转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但维新随之失败,收效甚微。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改革科举制度并再次下令书院普改学堂,“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被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以科举为目标的书院最终寿终正寝。清末,书院被迫改制为学堂,书院藏书不受重视,有学者指出,传统书院藏书多为经史类文献,不能满足培养新型实用人才的需求,书院藏书作用弱化藏书,“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长期的兵燹战乱成为书院藏书被迫散亡流转的客观原因。”山东书院藏书命运多舛,遭遇多重浩劫,其流转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管理不善,书院藏书逐渐散失。光绪二十九年(1903),冠县清泉书院改为学堂,书院藏书因无人管理,被县中士绅瓜分无存,“清光绪季年,吾冠购书百余种,皆精印善本,藏之清泉书院,自书院改为学堂,此书无人经理,累累卷轴,悉为士夫所攘据,邺架无存,此亦文物之憾事。”
二是遭遇战争灾祸,书院藏书毁于一旦。峄县峄阳书院的藏书在太平天国北伐时全部损失,“咸丰粤逆之乱,院毁于兵,存书亦尽散失。”博兴锦秋书院的藏书在民国时期遭遇兵燹而散失殆尽,“经民国十八、十九两年之乱,杂军、土匪肆意蹂躏,致将良吏前贤嘉惠后学之盛举销毁无存,等于秦人一炬,可慨也已。”
三是书院藏书归入当地新成立的公共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基础收藏。济南泺源书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制为山东高等学堂,1913年,山东高等学堂的藏书移交山东图书馆,成为山东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松林书院的藏书大部分为后来的青州一中所继承,青州一中即在原松林书院原址所建;临清州清源书院改制为学堂后,所藏书籍归县图书馆保存;夏津大同书院部分残存藏书在民国十七年(1928)也移交给县图书馆;民国初年,莒县城阳书院所藏书籍移交给新成立的县通俗图书馆。
六、山东书院藏书的历史作用
山东书院藏书在地区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国)重修博兴县志》纂修者曾高度评价博兴锦秋书院藏书的作用,“存置院中几四十年,阖邑士子寝馈其中,藉资博洽,甚盛事也。”书院藏书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书院藏书在书院教书育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大量人才
泺源书院以其丰富的藏书为书院师生学术研究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桑调元、沈起元、匡源、何绍基、缪荃孙、曹鸿勋等博学大儒在泺源书院讲学期间多有著作诞生,如沈起元为书院山长时,著有《周易孔义集说》,并将所研心得讲授于学生,书院生徒、历城人周永年“每于听讲后,荟萃注易家数十种,罗列几上,逐一阅之,既遍,起行庭中,默会之”;沈可培主讲泺源书院时,著有《泺源问答》,钱樾在该书序中说:“著《泺源问答》十二卷,上自十三经,兼综条贯,推阐无遗。其绪余更及于子史诸集,设疑辩难,融会贯通。”他主讲青州云门书院时,辑《云门书院志》四卷。泺源书院学规规定:“诸生于圣经贤传,固宜熟读详讲,以求旨趣,此外如列朝史册、诸家文集,均当以时分别讲读。”寿光廪生任象益在泺源书院肄业时,郑杲、宋书升、孙葆田、法伟堂等人先后任书院主讲,“郑吏部东父、宋太史晋之、孙京卿佩南、法征君容叔先后主讲席,咸以汉儒治经家法揭橥及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任象益遍览书院群书,“于大小戴、马、郑诸家解说,莫不探其奥窔”,编撰了《经字纂诂》一书,时人赞其为“《尔雅》之功臣,《字林》之宝鉴,非邃于经学、小学者不能也”。泺源书院培养出周永年、王懿荣、王寿彭、法伟堂等著名学者。临清州清源书院条规中规定:“平日修习各业分为四节,晨课阅览经史子集,及各国图书、各省日报;午课诵习《左》《国》《史》《汉》以下古文;晡课习楷钞书,不拘名目;晚课于官师两课月作六艺外,就日间阅读所得作为笔记,按十日汇呈教习评阅。”清源书院师生不只是练习科举制艺,而且广泛阅览文史群书,这得益于清源书院丰富的藏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川进士尹殿飏主讲清源书院时,“以六书课士,由是临人渐知小学,空疏学风至此一变。”可以说,书院藏书对于书院的教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书院藏书为寒门士子提供了宝贵的求学机会
书院的设立,有很大因素在于为寒门士子提供求学的场所,带有为国育贤的责任,如德州繁露书院的设立,时人盛赞:“洵为造福艺林,培养寒士之盛举也。”寿光知县吴树声“创建北海书院,寒士得庇。”古代藏书实属不易,花销很大,一般清贫读书人很难出手购买大部头的书籍。据晚清京官李慈铭日记,同治二年(1863),他购买《续通鉴》,用去60000钱(文),购买《尔雅义疏》《读书杂志》《南唐书》,用去26000钱(文);同治三年(1864),购买《汲版史记》《胡刻通鉴》《阮刻十三经》,用去24000钱(文),可以看出购置书籍是很大的开支。武城弦歌书院主讲叶锡麟言:“在院肄业寒士居多,苦志攻读,购书为难”,知县傅士珍为书院购置书籍三十余种,博兴知县李铨看到书院生徒苦于无书可读的现状。“寒士读书之难,读书而得善本之尤为不易”,在锦秋书院中置书数十种。书院藏书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大部头的类书、工具书,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三史等,卷帙浩繁,价格昂贵,非一般读书人和普通家庭所能购置收藏。官府动用公权力为书院藏书,可以说是解决了书院生徒读书的大问题。得益于商河县训导孙庆龄为麦丘书院购置数十种书籍,学子刘雯云“在书院三年,肆力坟籍,学识贯综,尤嗜读《通鉴纲目》,多所发明。”
(三)书院藏书保存了宝贵的古代文献
泺源书院藏书中价值最高、最为珍贵的当属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该书共分6编32典,分为5020册,520函,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此书在雍正六年(1728)仅印制了64部,非常珍贵,第二次印制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由此可见,泺源书院获得的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应是雍正铜活字本,但《(道光)济南府志》记载“一部四百八十五封”,与该书总规模不符,可能所藏该书并不全,但这样大部头的藏书在清代山东书院中也仅有泺源书院拥有,彰显了泺源书院作为省会书院的独特地位。据卢子扬《殿版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的流传与保护》介绍,山东图书馆所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4483册,就是泺源书院的藏书。书院藏书中官府置备的藏书大多为钦定、御纂书籍,特别是有不少内府版,如济宁新任城书院所藏《内府板十三经》《内府板二十三史》《内府板通典》《内府板通考》《内府板通志》,考订周密,刊刻精美,实为珍贵之古书刻本。泺源书院藏书中有不少珍稀刻本,如钱陈群《香树斋诗文集》、陈九川《陈明水集》、朱轼《朱文端公广惠编》、李来泰《莲龛集》等。明代鲁藩敏学书院所刻《张先生校正杨实学易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称其“刊印极精”,承训书院所刻《抱朴子》,其版式在明版中极为罕见。
七、山东书院藏书的不足
虽然藏书是书院重要的事业,但从史志记载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历代书院中一半以上的书院藏书不丰,甚至于很多书院没有藏书,凸显了山东古代书院藏书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发展不平衡、各级差距大等问题,山东书院藏书的不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明代心学书院与清代考课书院不重视书院藏书
明代书院中虽然一些个人创建的书院藏书很丰富,但从总体上看,书院藏书并不发达,这一问题多有学者讨论,如邓洪波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那些创造辉煌的书院建设者们对于藏书的态度上”;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及其后学,钟情于书院讲学、会讲,重悟性而轻积累,对书籍不甚重视。及至阳明后学空谈心性,束书不读竟成时尚,书院藏书终于滑入低谷。明代书院兴盛于明中期的正德、嘉靖年间,这也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隆庆年间,江右王学代表人物邹善提学山东,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讲学其中,致力传播王学,亲自创建济南至道书院、青州凝道书院、长清愿学书院,为昌邑养志书院、武城学道书院、平原闲道书院定名,为之撰记,赐予高苑高节书院牌匾,短短数年之间,阳明心学在山东得到快速传播。赵秉忠《云门书院记》记载:“隆庆丁卯,督学者邹公善讲明良知,羽翼圣道,设皋比函丈于此,一时贤哲师济景从。”在以传播心学为主的明代书院史料中,鲜有书院藏书的记载。正是因为心学家们重讲学而轻藏书,使得明代山东书院藏书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清代是山东书院数量最多的朝代,有研究者认为,清代山东书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理学书院、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考课式书院。考课式书院是指单纯或主要以考课为教学形式,以训练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的书院。乾嘉以后,山东各地兴办的书院大多是考课式书院。书院大多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书院内附建考院,或直接将书院当做考院,已经成为清中期以后很多书院的常见形式,如福山人萧铭卣所说:“邻封若栖霞、宁海,皆以书院为试院。”道光十四年(1834),新城知县李振先捐建的崇新书院,到了清后期,已专做考院使用。清人戴钧衡曾言:“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书院多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考课式书院往往只有考课而无教学,每月仅有官课、斋课等数次考试,平时书院生徒并不住院学习,只到考课时间到院考试,如高密通德书院条规规定,“书院为清净之地,无事封锁,不准闲杂人等游戏践踏,如有任意出入者,惟看院人是究。”此类书院平时没有师生,只在考课时开门,所以几乎没有藏书。班书阁曾指出:“书院所以教士者,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实。”
(二)清代省会书院与府州县书院藏书差距巨大
自书院诞生以来,书院经费一直是书院运转面临的重要问题,筹集书院经费是书院主持者永恒的话题。
济南泺源书院作为省级书院,在清代山东书院藏书中最为丰富,原因在于泺源书院的经费非常充足,据《道光济南府志》记载,泺源书院的经费如下:“雍正十一年,恩赏银一千两。乾隆六年,巡抚朱定元奏明捐银四千六十余两(铁抚规条云,续经公捐六千两,其一千余两何时捐,不详),俱交历城等九州县当商生息,岁解济东道库银一千五百五十两;嘉庆九年,巡抚铁保又公捐银六千两,盐商生息,岁共息银二千四百两有奇。道光八年,巡抚琦善又奏明历年积羡三千二百两,仍交商生息,并前共银一万六千二百两,岁收息银二千八百余两。”光绪十七年,书院山长缪荃孙《泺源小志》也记载:“书院经费,雍正间恩赏银千两,续经公捐银六千两,俱交历城等九州岛县当商生息,岁解济东道库银一千五百余两。今又公捐银六千两,交盐商生息,岁共得息银二千四百两有奇,仍责成济东道专司收发。”泺源书院共存藏书106种,大致可分为经学类、诸子类、程朱理学类、正史类、类书、集部文学类、科举应试类、地方志书类等等,仅《太平御览》就有十六套、《钦定佩文韵府》有十九套。济宁新任城书院为河道总督姚立德所建,因而书院得到了河道总督、济宁州、运河道等诸衙门的关照,经费也有保障,《(乾隆)济宁直隶州志》记载:“交当绅士乐输银三千两,按月二分起息,每年得息银七百二十两,遇闰加增,又续添旧书院银六百两,亦以二分起息,每年一百四十四两。”新任城书院的藏书多为知州蓝应桂置备,在济宁所有书院中尤为丰富,其中《内府板十三经》共十七套、《内府板二十三史》共七十七套、《内府板通典》六套、《内府板通考》十六套、《内府板通志》二十套、《御制佩文韵府》二十套,这样大体量的藏书,实在是其他书院无法望其项背,任城书院的藏书已经远超其他书院,“济宁旧有书院八,而新任城书院藏书尤富。”
清廷在省会书院与府州县书院两者执行了不同的政策,有学者研究指出:“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的确立以直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为主要标志,即以帑金、公项作为省会书院的重要经费来源”;“在经费问题上,清廷显然不愿加大对于府州县书院的扶持责任,而听任地方自行酌情办理。对于地方政府动用公共资产来作为府州县书院经费的做法,清廷表现得十分谨慎、保守。”这也就造成了府州县书院经费大多不足的现状。笔者研究发现,一个县一个时期往往仅有一所书院能够维持,而一直能够存在到清末的则更为稀少。乾隆五十七年(1792),博山范泉书院在创建者、知县武亿离开博山后,情况不容乐观,“创建之始,规模虽定,经费缺如,后之莅斯任者,每欲延师课读,而力有未能”;寿张县寿良书院自道光五年(1825)知县肖梦兰捐俸建后,“因经费无恒产,肖(梦兰)去课止”;咸丰九年(1859)临邑县犁台书院建成后,因无经费,形同虚设。州县书院经费如此拮据,有的府级书院经费也不宽裕,如泰安岱麓书院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建后,“日久,经费不足,废而不举。”登州瀛洲书院创建自康熙五十一年(1786),虽然有府属十州县的支持,但仍然是“岁租入不及百金,供山长修脯不足也。”在这样的情况下,书院生存尚属艰难,置备藏书已经属于比较奢侈的事情了。府州县书院藏书大多不丰,以置备最为紧要的书籍为主,以高密通德书院为例,书院仅有《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康熙字典》《四书汇参》《朱子全书》;淄川般阳书院藏书仅有《御纂四经性理》《钦定三礼疏义》《御制诗》,府州县书院藏书能够满足师生基本的研读需要和科举考试之需已属不易,不少府州县书院因财力短绌而无力藏书。单县鸣琴书院监院刘荣玺曾感叹书院没有款项可以购置藏书,致使学子阅读不广,“司监院者吾师刘信符夫子也,每言院中向无藏书,复以款项支绌,无力购贮,致肄业者有固陋之叹。”为了为书院置备藏书,地方官绅可谓穷尽脑汁。光绪年间,庆云知县夏声乔为了节省经费,兼任县古棣书院山长,“兼权山长,省款购置经史子集数百卷,备士子诵读。”与泺源书院相比,府州县书院在藏书方面的差距不可谓不大。
八、济南泺源书院、济宁新任城书院藏书之个案分析
(一)济南泺源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山东巡抚岳濬奉朝廷之命所建,是当时全国二十二所官办书院之一,也是清代山东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官办书院,其藏书之丰富位居全省书院之冠。
《(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七《学校》记载泺源书院藏书目录,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大体分类如下:
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四百八十五封、《太平御览》十六套一百六十本
经部:《钦定书经》六本、《钦定诗经》二十三本、《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本、《钦定仪礼义疏》五十本、《钦定周礼义疏》四十七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二十三本、《钦定春秋》二十四本、《钦定孝经衍义》一部三十本、《日讲易经》十八本、《日讲书经》七本、《日讲礼记》十六本、《日讲春秋》十六本、《日讲四书解义》十本、《易经注疏》一匣八本、《尚书注疏》一匣十本、《毛诗注疏》四匣二十八本、《仪礼注疏》二匣十八本、《周礼注疏》二匣十八本、《礼记注疏》四匣三十本、《左传注疏》四匣三十本、《公羊传注疏》二匣十二本、《榖梁传注疏》一匣六本、《孝经注疏》一匣八本、《孟子注疏》一匣十本、《尔雅注疏》一匣六本、《书经大全》十本、《毛诗疏》十九本、《仪礼疏》九本、《公羊疏》八本、《四书大全》三十二本、《御制律吕正义》五本
史部:《史记》二套十六本、《前汉》三套三十本、《后汉》二套二十四本、《三国志》一套十二本、《晋书》三套三十本、《宋书》二套二十四本、《南齐书》一套十本、《梁书》一套八本、《陈书》《周书》一套十二本、《隋书》一套十六本、《魏书》二套二十本、《北齐》一套六本、《南史》二套十六本、《北史》二套二十四本、《新唐书》五套五十本、《五代史》一套十本、《宋书》二十二本、《南齐》一套十本、《魏书》十五本、《南史》二套二十本、《北史》三套三十本、《隋书》十九本、《唐书》十八本、《宋史》十套、《辽史》八本、《金史》二套二十本、《元史》五十本、《通鉴纲目》四十五本、《纲鉴易知录》四十九本、《月令辑要》十二本
子书:《御纂性理精义》一部、《钦定数理精蕴》四十本、《钦定执中成宪》四本、《朱子全书》二十五本、《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三十二本、《二程全书》二十本、《文昌孝经注》一部二本、《庄子因》一套六本、《抱朴子》一套八本、《唐类函》十八本、《钦定佩文韵府》十九套
集部:《御制文集》一部四十八本、《万寿盛典》三十六本、《千叟宴诗》三本、《昌黎集》一部十本、《河南集》四套二十本、《苏文忠公诗合注》一部十六本、《王临川全集》一匣十二本、《蔡氏九儒》一套八本、《频伽围诗文集》一部六本、《阳明先生集要三编》一套十本、《四书求是》一部八本、《经义述闻》一部、《呻吟语节录》一部二本、《切问斋文抄》一部十本、《山左诗续抄》二套十六本、《朱文端公广惠编》一部一本、《李氏音鉴》一部四本、《香树斋诗文集》一部二套二十四本、《玉茗堂全集》一匣十八本、《陈明水集》一部六本、《莲龛集》一部六本、《鸟鼠山人全集》一部二十二本、《潜研堂诗文集》一部十八本、《空山堂全集》一部三十六本、《忠雅堂文集》一部四本、《忠雅堂诗集》一部四本
其他:《大清律》六本、《科场条例》十七本、《科场条例》四本、《旧济南府志》一部十六本
从以上泺源书院的藏书目录可以看出:
1、藏书目录基本上是只著录了书名、部数、本数,有的书籍是匣装,并作单独说明,但对于书籍的作者、刊刻、完残等信息则没有著录。《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前已说明,应有不少缺本;二十一史中,有《隋书》一套十六本和《隋书》十九本、《南史》二套十六本、《北史》二套二十四本和《南史》二套二十本、《北史》三套三十本等不少著录两个不同信息的书籍,其中有的版本可能有残缺,并非全本。
2、藏书目录大体上是按经史子集来分类的,涵盖了各个门类,特别是经史各部书籍比较全面,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一史等存书较多,这与清廷对于经史之学的倡导有直接的关系。乾隆三年上谕说:“士子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乾隆十六年上谕又说:“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序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乾隆帝曾钦赐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省会书院作为全省书院的表率、楷模,其藏书体现了朝廷的意志。有清在康熙之后,即着重在经史书籍标准化方面作出努力。康熙四十五年(1706),《古文渊鉴》《资治通鉴纲目》等书在康熙帝主持下编纂完成,即颁行各省,此后,《御纂性理精义》,《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等书编成,颁布各省,令各督抚、藩司刊刻颁发到各州县。泺源书院所藏经史各书,基本上是清代已刊定的、已标准化的经史书籍,这对于生徒参加科举考试非常有益。济宁新任城书院藏书中除去御纂、钦定书籍外,还有不少内府版刻书,如《内府板通典》《内府板通考》《内府板通志》,这三部书也是朝廷要求各省置办的书籍,但泺源书院藏书中却没有,不知何种原因。
3、泺源书院藏书中集部书籍是其藏书的一大特色,不只收藏有前代文人的文集,如唐代韩愈《昌黎集》、北宋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北宋尹洙《河南集》、明代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三编》、汤显祖《玉茗堂全集》等,还收藏了诸多本朝学者的研究著作,如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引之《经义述闻》、钱大昕《潜研堂诗文集》、牛运震《空山堂全集》、蒋士铨《忠雅堂文集》、朱轼《朱文端公广惠编》等。这部分书籍中又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经义述闻》此类经史研究书籍,二是《潜研堂诗文集》此类诗文书籍,但二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文史与诗文不能截然分开,如钱大昕的学术思想多体现其书文中。高邮二王、钱大昕等人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书院收藏他们的学术著作对于开拓生徒的经史视野大有裨益。泺源书院藏书中规模最小的是子书,先秦诸子及汉唐子书的藏书不多,《荀子》《管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子书不在藏书之列,尚不及博兴锦秋书院,其藏有一部《二十二子》、一部《汉魏丛书》。子书收藏的薄弱并不只体现在泺源书院藏书中,全省书院藏书基本都是如此。正如博兴知县李铨所说:“经史以槃深其根柢、子集以陶淑其性灵”,经史固然重要,子集也是不可或缺的。
4、虽然《济南府志》中没有记载藏书的来源,但藏书中有相当数量是官府颁发、朝廷赐予之书无疑,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御制文集》《万寿盛典》等。乾隆元年,朝廷下发上谕:“各督抚于省会书院,并有尊经阁之府、州、县,应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购买颁发,交与各该学教官,接管存贮,令士子熟习讲贯。其动用存公银两,仍报部查核。”泺源书院所藏经史书籍应该是官府动用公银置备的。书院藏书中还有《大清律》《科场条例》等法律、科举用书,这些都体现了书院的官学化,书院教学、藏书都在官府的掌控之中。
泺源书院藏书只在《(道光)济南府志》中有记载,而该志刊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也就是说书院藏书目录反映的只是道光二十年前书院藏书的情况,距离书院改制(1901)还有很长的时间,此后书院的藏书应有一定数量的增加,如书院刊印的课艺不在统计之列,特别是在同治九年丁宝桢创办山东书局后,大规模刻书印书,这些书应有一定数量入藏于泺源书院,可惜《济南府志》在道光之后没有续修,而《(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没有著录泺源书院藏书目录,因而泺源书院藏书在清后期的发展变化便无从得知了。
(二)济宁新任城书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驻济宁的河道总督姚立德所建,是济宁规模最大、藏书最丰富的书院。济宁,在清代应确切的成为济宁州,雍正二年(1724)和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次升为直隶州,领三县:金乡、嘉祥和鱼台,河东河道总督署驻地也在济宁,在济宁有三个主要衙门:河道总督、运河道和济宁州,因而济宁的书院建设得到了三个衙门的特别关照,得到的恩惠相比于其他州县要多很多,济宁曾创建8所书院,在全省名列前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八《建置志》记载了新任城书院的藏书目录:
《御纂周易折衷》二套、《御纂性理精义》一套、《御制佩文韵府》二十套、《韵府拾遗》二套、《渊鉴类函》二十套、《历代赋汇》十套、《全唐诗》十二套、《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套、《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四套、《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四套、《御选唐宋文醇》二套、《御选唐宋诗醇》二套、《内府板十三经》共十七套、《内府板二十三史》共七十七套、《内府板通典》六套、《内府板通考》十六套、《内府板通志》二十套、《国语注解》一套、《战国策》一套、《古文眉诠》四套、《宋诗钞》四套、《词综》一套、《尚书释天》二本、《济宁州志》一部、《济宁直隶州志》一部。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之一《学校志》所载新任城书院藏书与《(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相同,唯作“套”者皆改为“函”,如《御纂周易折衷》二函、《性理精义》一函,等等。
据姚立德《任城书院记》:“余莅河之三年,与兵备使吴江陆君谋所以扩充之,知州蓝君捐金改卜于城西南运河之滨、草桥之北,较之渔山,屋舍增三之二,而师生修膳之资亦几倍之,至经史子集与日用器具,皆无外求者,其用力亦云勤矣。” 姚立德创建书院的提议得到知州蓝应桂的大力支持,蓝应桂《任城书院记》记载:“于是相宅于西郊新司街,得王氏之居,捐金九百余两易之,而经史子集图书之藏、几案床榻之具、庖厨湢浴之所,并余之所营购也。”蓝应桂捐出九百余两银钱,买下王氏居宅,改扩建为书院,并为书院置备了经史子集图书,也就是说,新任城书院的藏书全部来自蓝应桂的置办。《(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刊刻于乾隆五十年(1785),开始编修者正是蓝应桂,续成于其后任胡德琳。蓝应桂将新任城书院的藏书全部记录在案,至《(道光)济宁直隶州志》编成之时(咸丰九年,1859),书院藏书并没有任何增加,《(咸丰)济宁直隶州续志》和《(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均没有记载书院藏书目录。《(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七《学校志》记载:“济宁旧有书院八,而新任城书院藏书尤富,亦丽正、集贤、睢阳、石鼓之遗也,往迹具存,悉载前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州邓际昌在新任城书院内设立师范传习所;宣统元年(1909),知州丁兆德又在书院设立初级师范学堂。新任城书院藏书随之流转,在民国之时,已成往迹,不再著录。
与济南泺源书院比较,可以看出济宁新任城书院的藏书在种类上要比泺源书院逊色,但其藏书规模并不小,如《内府板二十三史》就有七十七套(函),与作为省会书院的泺源书院藏书规模相当或在其上。蓝应桂记中说:“所颁四经三礼以及十三经注疏具在,无待外求,”可见,新任城书院的藏书以官府颁发的书籍为主,而其收藏的一套《战国策》,则较为特殊。《战国策》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清初学者陆陇其对《战国策》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因而书院少有收藏者。笔者认为,《战国策》的收藏,很可能与蓝应桂个人的兴趣有关。相较于泺源书院藏书,新任城书院藏书在子、集两部存书较少,这也应与官府对两方面书籍并不重视有关,有清一代,对于子、集两部的书籍并没有以御纂、钦定的形式进行编纂、写定,更没有下发各省,让各省刊刻、颁发,因而大多数书院藏书在这两方面都是比较薄弱的。
结语
自宋元以来,因为官学的衰弱,古代书院往往扮演了一个地区“斯文所在”的角色,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诚如《清史稿》所言:“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之不及……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尠也。”除了书院的讲学、课艺等活动,书院藏书可谓功不可没。
山东书院藏书是山东古代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聚了官方和民间对于书院教育的众多期望,这集中体现在官、民两个层面对于书院藏书的积极捐赠上;书院藏书对于地方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社会教化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现代图书馆事业和高校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1页。
[2]杨建东:《古代书院藏书概述》,《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5期;罗立、罗晓鸣:《古代书院的藏书制度》,《高校图书馆工作》2001年第4期;邓洪波:《简论中国书院藏书的五个来源》,《江苏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1期;肖永明、于祥成:《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徐寿芝:《古代书院藏书利用探析》,《图书馆杂志》2015年第10期;任蒙:《中国书院藏书事业考略》,《图书馆学刊》2018年第5期;吕艳:《中国古代书院藏书考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赵连稳:《中国书院藏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研究各省书院藏书的论文:赵连稳、王春福:《北京古代书院藏书探微》,《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吴莹:《古代河南书院藏书管理探略》,《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邱筇:《江西古代书院藏书事业尝析》,《江西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2期;陈明利:《清代福建书院藏书述略》,《福建史志》2014年第6期;雷成耀:《清代贵州书院藏书考略》,《安顺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胡立耘:《清代云南书院的藏书文化遗产》,《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5期。各省书院史研究专著中也往往有论及书院藏书的篇章,如张佐良等:《河南书院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20年;柏俊才:《湖北书院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张羽琼:《贵州书院史》,贵阳:孔学堂书局2017年版;吴洪成等:《重庆书院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吴洪成等:《河北书院史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4]贾秀丽:《宋元书院刻书与藏书》,《图书馆论坛》1991年第2期;李光生:《宋代书院藏书论略》,《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段玲玉:《宋代书院藏书研究》,黑龙江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邓洪波:《元代书院藏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葛立辉:《浅谈元代藏书的特点》,《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1期;邓洪波、樊志坚:《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江苏图书馆学报》1996年第5期;真理、胡长春:《试论明代书院藏书》,《江西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4期;韩淑举:《清代书院藏书初探》,《山东图书馆季刊》1988年第3期;李颖:《近代书院藏书考》,《图书与情报》1999年第1期。
[5]舒原、余峰:《中国书院的图书征集制度》,《湖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秦健民:《略论古代书院藏书与书院教学、学术研究的关系》,《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2期;王志勇:《清代书院藏书的借阅制度考略》,《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王志勇:《清代书院藏书的购置与分编著录》,《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周郁、蔡建国:《晚清书院藏书图书馆化述论》,《高校图书馆工作》2008年第2期。
[6]王立斌:《鹅湖书院历代藏书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叶宪允:《毓文书院藏书考》,《贵图学刊》2012年第3期。
[7]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
[8]王炳照:《中国书院史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年,第151页。
[9]赵承福:《山东教育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0-432页。
[10](明)杜思修、冯惟讷纂:《(嘉靖)青州府志》卷九《学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
[11](清)颜希深修、成城纂:《(乾隆)泰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1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14](清)高其倬、谢旻修,陶成、恽鹤生纂:《(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艺文记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十四《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2-2033页。
[16](明)栗可仕修、王命新纂:《(万历)汶上县志》卷二《学校》,清康熙五十六年补刻本。
[17](明)栗可仕修、王命新纂:《(万历)汶上县志》卷八《艺文志》,清康熙五十六年补刻本。
[18](清)汪鸿孙修、刘儒臣纂:《(宣统)重修恩县志》,第135页。
[19](明)陆釴纂修:《(嘉靖)山东通志》卷三十四《流寓》,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20]邓洪波:《元代书院藏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1](清)吴璋修、曹楙坚纂:《(道光)章丘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27页。
[22](清)凌绂曾修、邵承照纂:《(光绪)肥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3](清)祖植桐修、赵昶纂:《(康熙)朝城县志》卷二《疆域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24](清)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25](清)祖植桐修、赵昶纂:《(康熙)朝城县志》卷二《疆域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26]邓洪波:《简论中国书院藏书的五个来源》,《江苏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1期。
[27]赵连稳:《中国书院藏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28](明)陆釴等纂修:《(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六《学校》,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29](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77页。
[30]《清世宗实录》,《清实录》(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5-666页。
[31](清)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64-366页。
[32](清)徐宗幹修、许翰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7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33]刘佑纂修:《(光绪)高唐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8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69页。
[34]朱兰修、劳乃宣纂:《(民国)阳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3),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35]谢锡文修、许宗海纂:《(民国)夏津县志续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31页。
[36](清)方学成修、梁大鲲纂:《(乾隆)夏津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6-57页。
[37](清)汪鸿孙修、刘儒臣纂:《(宣统)重修恩县志》,第135页。
[38](清)祖植桐修、赵昶纂:《(康熙)朝城县志》卷二《疆域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39](清)胡德琳修、李文藻等纂:《(乾隆)历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40]余友林修、王照青纂:《(民国)高密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93页。
[41]杨豫修、郝金章纂:《(民国)齐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3),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42]苗恩波修、刘荫歧纂:《(民国)陵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44页。
[43]谢锡文修、许宗海纂:《(民国)夏津县志续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31页。
[44](清)张同声修、李图等纂:《(道光)重修胶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21页。
[45](清)李敬修纂:《(光绪)平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28-429页。
[46]武振伟:《试论明清时期士大夫与山东书院建设》,《海岱学刊》第25辑。
[47](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第186页。
[48]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468页。
[49]王陵基修、于宗潼纂:《(民国)福山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50]王陵基修、于宗潼纂:《(民国)福山县志稿》,第186页。
[51]侯光陆修、陈熙雍纂:《(民国)冠县志》,第76页。
[52](清)刘文煃修、王守谦纂:《(光绪)寿张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93),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
[53]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144页。
[54]孟鸿声:《泺源书院志》,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年,第409-412页。
[55]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第1325页。
[56]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第1316页。
[57]孟鸿声:《泺源书院志》,第235页。
[58](清)凌绂曾修、邵承照纂:《(光绪)肥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59](清)厉秀芳纂修:《(道光)武城县志续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60]王鬴铭纂修:《(民国)增订武城县志续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26页。
[61]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73页。
[62](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纂:《(乾隆)淄川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63](清)刘文煃修、王守谦纂:《(光绪)寿张县志》,第372页。
[64](清)刘文煃修、王守谦纂:《(光绪)寿张县志》,第509页。
[65]张其丙修、张元钧纂:《(民国)重修博兴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66](清)罗邦彦、傅赉予修,李襄运纂:《(光绪)高密县志》卷五《学校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67](清)周尚质修、李登明纂:《(乾隆)曹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8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68](明)宋濂等:《元史》,第2033页。
[69]武振伟:《齐鲁先贤名宦遗迹与山东书院建设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
[70](清)王植修、张金城续修:《(乾隆)郯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71](清)王植修、张金城续修:《(乾隆)郯城县志》,第104页。
[72]栾钟垚修、赵仁山纂:《(民国)邹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73](清)张思勉修、于始瞻纂:《(乾隆)掖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6),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74](清)胡德琳修、李文藻等纂:《(乾隆)历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75]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50页。
[76]张梅亭修、王希曾纂修:《(民国)莱芜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7-78页。
[77]王鬴铭纂修:《(民国)增订武城县志续编》,第626页。
[78](清)胡德琳修、李文藻等纂:《(乾隆)历城县志》,第230页。
[79](清)王振录修、王宝田纂:《(光绪)峄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80]朱兰修、劳乃宣纂:《(民国)阳信县志》,第107页。
[81](清)刘佑纂修:《(光绪)高唐州志》,第369页。
[82]张其丙修、张元钧纂:《(民国)重修博兴县志》,第84页。
[83](清)祝嘉庸修、吴涛源纂:《(光绪)宁津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84]余友林修、王照青纂:《(民国)高密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93页。
[85](清)祝嘉庸修、吴涛源纂:《(光绪)宁津县志》,第96页。
[86](清)刘佑纂修:《(光绪)高唐州志》,第369页。
[87]邹桂香、高俊宽:《我国近代书院藏书的流转与传承》,《图书馆》2021年第10期。
[88]侯光陆修、陈熙雍纂:《(民国)冠县志》,第76页。
[89](清)王振录修、王宝田纂:《(光绪)峄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90]张其丙修、张元钧纂:《(民国)重修博兴县志》,第84页。
[91]光绪二十八年(1902),松林书院改为青州官立中学堂。民国三年(1914)又改为山东省第十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山东省立青州中学。此后数易其名,1986年,正式定名为青州市第一中学。
[92]张其丙修、张元钧纂:《(民国)重修博兴县志》,第84页。
[93]毛承霖纂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76页。
[94](清)沈可培:《泺源问答》卷首,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95](清)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第367页。
[96]宋宪章修、邹允中等纂:《(民国)寿光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
[97]张自清修、张树梅等纂:《(民国)临清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9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98]张自清修、张树梅等纂:《(民国)临清县志》,第62页。
[99]李树德修、董瑶林纂:《(民国)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100]宋宪章修、邹允中等纂:《(民国)寿光县志》,第161页。
[101]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20、121、128页。
[102]石毓嵩修、路程诲纂:《(民国)商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1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
[103]卢子扬:《殿版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的流传与保护》,天津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104]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第99页。
[105]邓洪波:《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江苏图书馆学报》1996年第5期,第47-48页。
[106]武振伟:《明儒邹善提学山东及其王学思想探析》,《国际儒学论丛》2020年第1辑,第124-134页。
[107](清)张承燮修、法伟堂纂:《(光绪)益都县图志》,南京: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3),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108]马学强、赵树廷:《清代山东书院的发展研究》,《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
[109]王陵基修、于宗潼纂:《(民国)福山县志稿》,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2),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110](清)罗邦彦、傅赉予修,李襄运纂:《(光绪)高密县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112]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465-466页。
[113]姚伯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稿本<泺源小志>》,《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年第3期。
[114]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7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115]赵伟:《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研究(1644—1850)》,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
[116]王荫桂修、张新会等纂:《(民国)续修博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117](清)刘文煃修、王守谦纂:《(光绪)寿张县志》,第371页。
[118]葛延瑛修、孟昭章纂:《(民国)重修泰安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6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
[119](清)王文焘修、张本纂:《(道光)重修蓬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120]项葆祯修、李经野纂:《(民国)单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8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20页。
[121]秦夏声修、刘鸿逵纂:《(民国)庆云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122](清)素尔讷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第20、21页。
[123](清)素尔讷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第18页。
[124](清)胡德琳修、蓝应桂续修,周永年、盛百二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八《建置志》,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125]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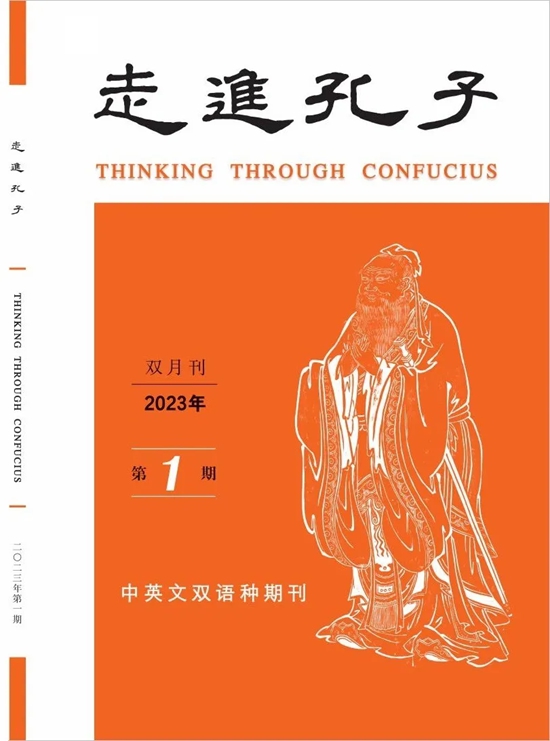
本课题报告的阶段性成果已于2023年刊发在《走进孔子》第1期。
项目批准号:22ZBSKB035
项目负责人:武振伟
所在单位:齐文化研究院
初审编辑:田泽文
责任编辑:李玉梅